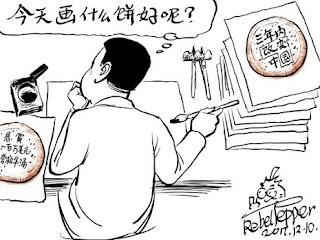为什么说顾晓军名气很大?
太阳地
--顾晓军小说•之一(一卷:太阳地)
太阳,没有轮廓;燃烧成灿烂的一片,辉煌、且耀目。
太阳光,猛揉草地不止;竟将绿色草,揉成一簇簇蓝色的火苗。
沼泽湖灸痛了,默然无声,任郁苦与微香抖抖地飘升;似草地上一只只美丽的眼睛,沉积着无数忧伤的故事。古老,又新鲜。
起微微一丝细风,却吹不起沼泽里那绿水半点涟漪。于是,焐热的草地上,便有了些绝望的寂寞。
远处,有小小一个黑点,在渐渐放大、慢慢移来。
小黑点的后面,歪歪斜斜地迤逦着两行微微浅浅的脚印。足印浅浅,自然斟入的阳光也就浅浅。
但,此时的草地,毕竟有了些生气。
小黑点终于放大、终于移近,且显现出了轮廓。
那草灰色的衣裳黯然,似有意作锃亮的铜号的陪衬。铜号一晃一晃,将束射的阳光反弹出去一片,似散射的乱箭。
金子般的号上,系红绸一穗;悠悠中,劈呖呖如燃烧。这样,便又烧去了草地上好些绝望。
不断移动、不断放大,方才看清那草灰色的衣裳,竟是一套军装。而撑起这套军装的,却还是个孩子。
许是饿乏了的缘故,那八角帽下的小脸,很瘦很黄,且脏。
东张张,又西望望。孩子显得很大很大的眼球,似要跌落出来。自然,他是在搜寻着什么。
而地上,只有五颜六色的花、与草、与他自己很短很短的影子。
抑或是失望、抑或是疲惫,孩子一屁股坐下来歇憩。两腿叉开,一双穿草鞋的脚,倒不小。
他自近向远,将目光推移,依然仔仔细细地搜寻。
四周,只有各色花,一盏、又一盏……如诗如歌地灿烂!
能果腹的野菜,是很难寻得到了。草地虽大,但已经篦了几遍。单他记得,就来回走了两遭,如今才又折回来。
天涯里,似有人声;而他,不曾听得,只痴痴地抚心爱的铜号,想那清水煮野菜的滋味。
爸爸是能干的。虽无油缺盐,却也能将那一棵棵飘在沸水里的野菜,做得很香、很香。
孩子饿极了,便觉得那汤似山珍;自然,他并不知道山珍是何味。
而他的爸爸,又总是只呷上一口,便端了来,倒给儿子。爸爸淡淡地一笑,慈眉如残月。
于默想中,一线涎流了出来。
“馋虫!”一朵浅浅的笑,凄然地开。
孩子站了起来,弯腰去拾铜号;抚净了灰尘,仰头看一看天,又在太阳地里走。眼睛,依然睁得老大老大;目光,扫去扫来。
沼泽湖,截断了花路。
他才觉着了渴,便蹲下去……凝眸一看,只见那水如七彩云霞。红的,似一汪桃花汁;绿的,象一泓翡翠液……似融,又不融;却很醇,象酒。
他推目向远,又见一片片油花花泊定,形同罗绮;舔了舔唇,他杵着膝盖直立起来。
欲去时,才发现身边长着一圈五色的毒菌。
“这漂亮却害人的东西!”
他撒出一股子尿,去击。看大珠小珠跳起,又溅落;一沟白沫滋滋地叫着,欢欢地流去。
寂寞中,有了歌声;死水里,也有了涟漪。他,陡然有了些快意。
咦!
眼睛里,跳进了无数星星;确切的说,是一片灿烂!
偶尔抬头举目,他便看见那璀璨如金子的一片。
不远处,金黄金黄似葡萄般大小的野果子,一簇串一簇串地在草墩上、在花丛中,招他。
其时,孩子便想到了爸爸高兴的样子。
也是,原来爸爸领着好多好多的人马,而今只管十几个人的肚子了。爸爸心急的,他怎么能不心急?
爸爸去找野菜,叫他也远远地去找;自然,是要多多的。“去,听话,带上你的小铜号。”
孩子自然高兴,也奇怪。平时,爸爸是不准我走远的,尤其是一个人;而今天,却不同了。
这,说明我已经长大了。孩子,凄然地一笑。
长大了的孩子,便知道要替大人分担些什么。他,自然也知道;望着那葡萄似的金黄金黄的野果子,心里很甜很甜。
“贼滑!”孩子跳到一个草墩上,颤颤地闪忽了几下,在绿草上立稳。
软软的,象踩在一团忽忽悠悠的棉垛子上;心,别别地跳。
沼泽湖里的这些个草墩,大多是草根与泥炭合成的。踩上去,就象是踩着了陷阱;或许,一脚就下去了,且无声无息。
能管十几个人的一天呢!爸爸肯定敢上!
他想。爸爸敢上的,我也一定要敢上。人小、身子轻,不会有事的;且是用力地跳,轻轻地踩,会有什么事呢?
象蛤蟆似地鞠着,一跃、一跃地……他竟靠近了去。
居然,如他的想象――平安无事,上了人间仙岛;不,是花果山!
这回,爸爸可要高兴了。他,似乎己经做成了一件大事。
我,真的是已经长大了,也会象爸爸一样的。他没舍得往嘴里放一颗,先去脱上衣,准备盛果子。
真叫人高兴死了!他,极小心地忙着,心里比吃了果子还甜。
金子般的铜号,滚了起来;这,无疑是要去抓的。
不好!可已经来不及了。他一脚踏空,“噗嗵”掉进了沼泽。
臭水,狂笑着没到了腰间;淤泥,张大嘴咬住了双腿。
嗨,你放!你,放不放?……挣扎着、扑腾着,大口大口地喘气;他,呼吸渐渐困难……且,越来越难。
完了!他将抓到手的铜号,赶紧举过头顶。
“真见鬼了!”
在粘腻腻的淤泥中,他的脚竟踩到了一个圆圆硬硬的东西,象是个死人的骷髅头。
还有救!他拼命地去扒草墩,将手指嵌进蒲草的根须里。
终于,稳住了身子,且不再下沉。
就这么立着?自然不!将身子提起一点点。但,两腿却不能动。淤泥怎么也不肯放他去。
一次、二次、三次……徒劳!
只有手指扒拉下来的草根,在渐渐地增多,慢慢地覆盖了身边那已浑如黑牛乳的水面。
力气,也似那蒲草的根,一点一点地被扯碎,一点一点地飘在水面上,随那一轮一轮的涟漪漾开去。
无计可使。且,脚底下的鬼头,竟躲躲闪闪,有恃无恐。不如立着。
吹我,你吹我啊!你爸爸听见我的声音,一定会来救你的。
阳光,在铜号上炸开……铜号,这么对他说。
爸爸多好啊!这时,他才好象明白:爸爸,为什么总是要他把铜号带在身边。
将铜号贴近嘴唇,他用胳膊肘杵着草墩。
吹集合号?可,爸爸是不准随便吹它的啊!他想,爸爸是一定会找来的。我不吹号,他也会找来。爸爸自有爸爸的办法。
他,发现自己所在的沼泽,地势并不低;顺着茂盛的乌拉苔草的地平线,在五颜六色的野花的颈间,能望出去好远、好远。
大草地,实在是太美了!就象是我们的中国……所以,小鬼子要眼谗。
孩子想,爸爸说得多好!
但,这一滩滩污泥浊水与那一簇簇漂亮却害人的东西呢?象什么?自然是反动派、卖国贼!孩子,这么想。
他,独自,在沼泽中、在死水里。
太阳光,将淤泥中微苦郁臭的气息,一丝一丝地抽出来,又一团一团地往他的鼻孔里塞。
他,又觉出饿来了。
但,那金子般诱人的野果子,是够也够不着的了。刚才,怎么就没有先吃它几粒?真后悔!
孩子,毕竟是孩子。
活着,多好啊!
清澈如洗的蓝天上,有一只雄鹰在盘旋。
它,侧身斜翅,一圈、一圈地往上升……直到成了小小的黑点一个,直到一个小小的黑点也不让人看见。
许久、许久……他,才收回目光,去望自己的铜号。
铜号依然锃亮,只是穗子湿了;但,红绸越发彤红,真的似火了。
他有了点力气,便用胳膊肘杵着草墩,将胳膊构成三角形,把铜号移到眼前,对准太阳望去。
太阳光,从喇叭口聚拢来;似千万支金箭,直射他的瞳仁。那金箭,就象射在玻璃球上;而后,再弹起。
他,顿觉昏眩,赶紧闭上了双目。
许久、许久……眼前,却不是黑暗一片;而是一片灿烂的金花,在开放、在闪烁,绚丽非常。
过了好一会,金花才渐渐凋谢。
睁开眼睛,去看世界;世界,却是依然一片……他,陡然有了些恐怖;四周,也是一种绝望的死寂。
不能,决不能就这么沉沦……必须,必须打破这寂静、这死一般的寂静!
吹号?吹!
把铜号对准嘴巴。胸闷、气紧,他憋足了力气,腮帮子鼓涨得通红通红;这,才迸出一串号音:
“哒……哒……”
号音,远去。
远方,有“叭”地一声枪响,撕破草地上的沉寂,象是回应他凄然的号音。那枪声,也很凄然;隐约中,还有惨然的呼喊。
“秋子――”
那呼喊,象是从正在沉陷的胸腔里挤出来。这是爸爸的声音。爸爸也在沉陷?
“爸爸――”他,发出撕心裂肺地呼喊。
号声――
枪声――
“秋子――”
“爸爸――”
沉陷了。一切声音,都在死寂的草地上沉陷了。
“爸、爸!爸――爸――”童稚的呼喊,再一次在死寂的沼泽里发出,在天底下放大。
他一冲动,平衡打破了。
脚底下的骷髅头,也不知躲到了哪里去。湖状的淤泥,突然变得异常的有力;象一个蛮汉子,在下面抱住了他的双腿,死劲地往底下拽。
薄薄一层死水,居然也咆哮起来,似狂涛要覆没他。
他,还想喊,还想呼唤爸爸。但,没有来得及出声。一串咕噜噜作响的水泡,冒了上来……小鬼,捉住了他。
不能让它跟我一道沉没!铜号,划出一道金色弧,从他的手中飞出。
死水如沸,翻腾了许久;漪沦如波,漾漾了许久。
然,那铜号,却没有沉没。
红穗依然如火,劈呖呖如燃烧!
铜号,倒立着,似一朵黄玫瑰怒放,在沼泽上。
原载《小说选刊》1987年第一期